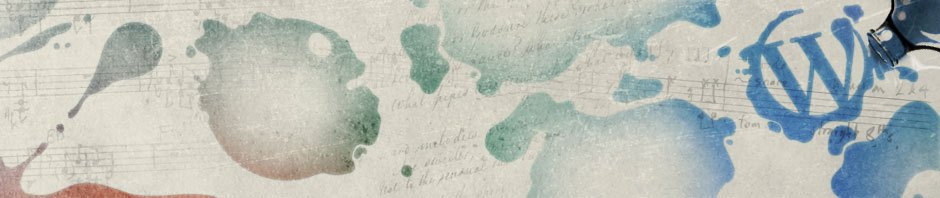-
Recent Posts
Recent Comments
- ZhangYimo on 蛇年拜年
- ZhangYimo on 两天强制休息
- ZhangYimo on 2024年春节的自动回复
- ZhangYimo on 错在哪?
Archives
- May 2025
- April 2025
- March 2025
- February 2025
- January 2025
- December 2024
- November 2024
- October 2024
- September 2024
- August 2024
- July 2024
- June 2024
- May 2024
- April 2024
- March 2024
- February 2024
- January 2024
- December 2023
- November 2023
- October 2023
- September 2023
- August 2023
- June 2023
- May 2023
- April 2023
- March 2023
- February 2023
- June 2021
- February 2020
- May 2019
- October 2018
- July 2018
- May 2017
- March 2017
Categories
Meta
Author Archives: ZhangYimo
公益机构不合作的怪圈
这个标题多少有点夸张,不过弱势的公益机构确实不够团结。公益机构其实有很多合作,比如一起发起一个联盟,或者一个大的平台机构与一些开展项目机构的合作,甚至也有公益机构之间的“并购”,互动很多。但仔细想来,很多同行机构(比如环境机构)其实愿景都差不多,而且差异化的行事方法和风格既形成了不同的专长和个性,也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然而,现实工作中,却鲜见两个相关机构合作的案例(或许是我本人孤陋寡闻),所以思考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 为了更好地为合作分类,我把公益机构和商业领域作作对比。 第一,同行业企业的合作。有一些同行,诸如各个航空公司,形成三大联盟,一群同行(至少表面上)抱团死磕另一群同行,是典型的合作,各自拿出自己的特长(即本国航权)来和别的同行合作,这样的合作通常只能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存在。这些联盟类的合作在全球的公益圈都几乎不可能实现。 更常见的合作出现在行业协会,通常是为了更大发声以争取政策支持,公益机构也有不少相似做法,比如零废弃,环境教育等等。这类联盟在推动他人改变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也对达成联盟的目的有效,不过不管是商业还是公益,此类联盟若无强大的秘书处来推动竞争,除了分享学习经验,对成员个体无甚帮助。所以这种合作其实是有的,但是和我们想看到的合作有一定距离,所以姑且不算吧。 第二,平台和商家的合作。本身这种合作由来已久,传统上,比如广交会等大量的政府主导的平台,或者由沃尔玛或者太平洋百货等把门店当平台吸引品牌入驻,而自身负责推广的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愈加主流化。天猫是国内最典型的例子。从这方面讲,扶贫基金会等中字头机构,以及腾讯公益等做得也很主流。对于平台来说,主导广交会的政府挣到了业绩,盈利为目的的沃尔玛挣到了钱,而扶贫基金会和腾讯公益虽然挣到了影响(当然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却没有因此在自己关心的领域上有直接的产出。所以这个合作仍然不能真的算合作。 第三,垂直行业的合作。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麦当劳就只卖可口可乐的产品。而肯德基只卖百事可乐。说到这里,读者肯定会立即指出,百胜本来就是由百事控股的公司,肯德基卖百事,母公司自然有更大利润。所以这个例子不能算合作!但转念一想,如果可口和百事不是那么同质,而是差异很大,大到肯德基卖可口可乐的利润,高于卖百事可乐时,百事饮料公司和百胜公司的利润总和,那控股母公司会不会转卖可口可乐?我相信答案是“肯定会”。所以这个是合作,是利润为导向的合作,是有股东的利益塑造的合作。 在这个意义上,公益机构倒也有正面例子,即两个个体公益机构相互合作。这背后的最好的驱动力,恰恰是同时担任两个机构理事(或者起极大作用的人物)的个人促成的。例如两马就曾促成某国际机构和国内机构的合作。互相利用对方的身份便利,这,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当然,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这种合作并非出于专长,而是身份,从而导致两个机构不可避免地一度共同协调管理,那这种内化的合作,是不是还是一种合作呢? 总体而言,在中国,由于业务相互互补而自动走到一起的同行机构几乎没有。所以,要使得公益行业中的差异个体开展合作,看起来还有很长路要走。但是,这种合作是不是先天就不可能?或者有太多的因素阻碍着它发生呢? 也许是理想主义的天生悖论。
摒弃一次性塑料的年中总结
现在距离年初的新年愿望——有条件地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已经过了半年。与其说这是半年摒弃(一种戒绝的行为),更像是一种自我观察,以及对全球塑料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思考。 我年初说的有条件摒弃,主要排除的是许多和食物、包装等无法回避的情况。现实情况是,正是由于这一些原先认为可以“例外”的方面,我仍然使用了大量一次性塑料。一下是具体。 成功戒绝塑料的方面: 1 主要包括一次性的塑料餐具。只要随身带筷子和杯子,基本不需要再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主要的场景包括:无需使用餐馆提供的一次性碗筷(通常他们还要收两元钱!),接受自带杯的咖啡馆(比如Starbucks),以及塑料包装的饮料(可以喝易拉罐,不买塑料瓶)。 2 购物也是一个可以省去袋子的场景,超市里面自带环保袋已经是很多人的标配了。如果进一步,在买超市生鲜的时候,都用自己的袋子,也可省去很多一次性塑料。 3. 工作需要我频繁出差,自带重复灌装的洗漱用品可以省去大量宾馆一次性用品(因为我都住经济型连锁,其实那些一次性用品质量也很糟糕)。 4 不叫外卖,当心快餐。外卖大量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看到别人丢弃的时候都觉得恐怖。而快餐通常只有饮料是塑料包装的,汉堡、薯条、鸡腿、派等都是纸包装,可以自己带上水或者听装饮料,去买皇堡和麦乐鸡。 简言之,亲自吃饭+一副自带的筷子、杯子和饭盒,可以解决生活中80%的一次性塑料。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一切都离零一次性塑料差得很远。 1 如果不用一次性塑料,基本就告别了所有零食了。虽然不吃零食并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但关键问题是,这一信息无法有效传递给食品制造公司。我无法举着手里装着山楂球的纸袋子,告诉隔壁卖鱿鱼丝的人,说我不买你的鱿鱼丝,不是因为我想吃酸的,而是因为你用塑料包装。而且零食公司(以及大量包装食品的公司)也很清楚,几乎不会有人愿意为减少塑料转而使用其他昂贵替代品而买单。 我收集了一下,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一次性塑料(尽管年初已经有所预计),一个月约80克。远超原先的预计。 2 在外出差、开会时,只能喝宾馆里的包装水。每次拧开都会有很强烈的罪恶感,但又没有别的办法(毕竟不是每个地方的水都可以烧了喝的)。 今年迄今为止大约消耗了50瓶包装水,都是宾馆里的。 3 航空公司大量使用一次性塑料包装,大家都看得到。由于飞机餐只能是隔夜饭,米饭烧熟,冷却,再加热,因而口感非常糟糕。而考虑到这个过程中所需要增加的油脂以及盐分,在机舱里吃饭既不健康,也不享受。只可惜我每次拒绝飞机餐的时候,总觉得那些塑料和食品最终是被白白丢弃的…… 4 快递是另一个问题。通常工作中寄送的都是文件,基本没有塑料。无可避免的是网购。填充料、封箱带、塑料袋等,都是一次性塑料。这些都是便利的代价。 针对这些观察,解决方案可以包括, 1 对于不必定需要的食品、化妆品等,如果特别想买,第一要鼓励反复使用无可避免的塑料包装,避免一次性使用。塑料有很多重要的价值,除了便宜以外,保鲜、轻质、防水应该是最主要的优势了。既然不能避免,就应当鼓励反复使用。对无法做到反复使用的情况进行惩罚,并加强措施,鼓励回收。这一些,是政府可以出政策,NGO可以竖榜样的。 2 商业设施(例如宾馆等)适当提供免费或者投币出水的饮用水,这是减少包装用水的简易做法。投资净水设施就可以解决不少问题。事实上,这样的管理成本也可以小很多,只需要定期换净水设施,而不再需要挨家挨户送水。何况一个房间两瓶水,一整撞宾馆可能一天就要好几千,还不算可以省下的工人工资。 3 既然航空公司在飞机上提供餐点是航空公司和乘客双输的情况,即顾客需要花很多钱(考虑制作、冷却、运输熟食、食品过安检、食品本身和推车造成的飞机重量增加)来吃并不好吃的飞机餐,航空公司又不得不准备这些内容(因为这个是通行的服务配置),从而需要雇佣额外雇员或者外包给其他公司。解决方法不难,就是让旅客事先选择是否需要餐食。既然中国的机票价格是固定的,折扣不容易直接体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不要餐食的旅客多一些积分。这一些,是航空公司直接可以做的。 4 相比于网购,更应该亲自买东西。我通常的做法是,只要实体店的价格比网购贵在10%以内,就在实体店里面买。除了省掉快递一次性塑料,去实体店有更多好处:上街除了让城市更多充满活力,减少横冲直撞的电动车;由于出门比较麻烦,而且支付的时候对价格更敏感,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消费。
日语初学感触
去年年初又萌发了学语言的春心。再学习罗曼语呢,边际效应已经很弱了;闪含呢,却要重新背一套新单词。思来想去,于是就把手伸到了霓虹国。可惜去年至今也只是断断续续地看沪江网校的课件,既没有时间练习也没有时间总结,所以现在只是草草将一些经验总结出来,待以后补充详细。 现代汉语的大量词汇来源于日语,早已众人皆知。我们今天所用的大多数新兴词汇,尤其是抽象的词汇,基本是从西方进入日语,此后又从日语所用的汉字传入中国的(就以上两句话而言,用到的日语词是:現代,大量,語彙,大多數,新興,抽象,基本)。而还有部分词汇,是彻底改变了汉语的原意,“经济”原来是治国之方,现在受了日语的影响,已经用来表达原先的”货殖“之意。同样,“科学”原来是科举之学,现在受了日语的影响,用来表达原先的“格致”之意。好基友“赛先生”穿上了和装,本该穿长衫的“德先生”也改头换面,自称“民主”桑了。 当然,这也就是一个中性的现象,当中应该有各种原因:硬件方面,内因确是因为晚清的中国文化不仅处于历史盛衰规律的低谷期,外因是又恰逢西方新鲜事物(总归要为每一样没看见过的东西起个名字吧)和概念大量涌入,两个一叠加,就有了对于新词汇的强烈渴求。软件方面,日语用的是汉字,拿过来简直没有任何障碍。一来一去,就让这些日语词长驱直入,加之新文化运动前就有人要求“我手写我口”,不仅把人们从古书的思想解放了出来,更加是打破了书面语和口头语的隔阂,让这些词能够方便地流传开来。这一点事实不应该引起仇日人士和民粹人士的反感,如果真的有反感,他们可以巧妙地避过所有日本词来表达他们的理想。况且同样的事情也多有发生,法语当年在百年大战的时候给英语送去了很多词汇,而如今却不得不用CD、Internet等纯粹的英语词生活;而希伯来语大量借用阿拉伯语词汇,不消说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不和显然比中日更深远。 以上是日语对汉语的影响。但反过来,日语受到的汉语(主要是吴语)影响则更为深远。日语和吴语的相似性确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其清辅、尖团、入声、变调几乎与吴语完全一致。其原因是,日语的音读汉字大量采用“吴音”(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唐音”),即公元5世纪前后慢慢从吴地输出,所以与今天的吴语仍然保持着高度一致。一个汉字,用上海话读出来,再经过一个相对固定的函数变化 (因为日语音素较少而吴语是全世界音素较全的语言之一,所以”吴语–->日语”可以对应,反之则比较困难),就是其日语的发音。例如某条规则是,1. 上海话的/k/ (相当于拼音k)和/k’/(相当于拼音g)对应日语的/k/,2. 上海话的/z/ (普通话无此音)对应日语的/z/,3. 入声音对应日语的”-く”或者”-つ”。那么以“家族”一词举例,上海话读作:“ka” (团音平声);“zo”(尖音入声),则日语”家族” 发音为:かぞく(kazoku)。“ka”对应的是团音清音的“家”,“zo”是尖音浊音,“ku”用于浊音后表示入声声调(清音后用,tsu)。顺便,在变调方面,“家族”一词,上海话必需将重音放在“家”上,轻读“族”,日语也完全一样,重音在“家”且不可更改重音。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仍在总结中。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看到日本人会有那种说不清的感情了。我们两千年来都是他们的老大哥,对他们输出了灿烂的文化,近代我们却收到了他们反向的文化输入。而侵华战争和最近的右翼势力是中国人无法容忍的,可他们现金生产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又让我们的老百姓心动不已。怪不得鲁迅先生当年就有“拿来主义”的倡议。这样的思考,直到今天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Reunion With Fellas
This is a friendship dating back to 1994. We shared so much fun, yes, almost only joy and happiness. However, we have had so few chance to meet since Vincent left China in 2005. This time in 2017, we managed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家|Family, 英|English
Leave a comment
开张志喜
“烟酒糖茶咖,吴北英德法;音体戏自趣,身游心思遐。” 我多少也算是个喜欢寻自己麻烦的人,也喜欢瞎想八想。十年前,MSN Space还可以嫌贬QQ空间的时候,我也涂过几年的鸦。无奈后来MSN成功诠释了“每况愈下”,每次升级都一版差比一版,所以弃用以后,博客也不知道搬到哪里了。 前几年注册了这个实名域名,上一次用只是2014年为了低碳地发结婚请帖,短暂开了一下网站。过了两年多,总觉着这么好的域名不用作个人博客也是蛮可惜的,就一直想着要重建。可惜最好用的几个傻瓜网站,不是被屏蔽(blogspot),就是被干扰(weebly),所以反复研究之后,基于wordpress做了这样一个设计简陋,功能尚薄的博客(注1),算是给自己留一个自言自语的空间。 博客名字叫做小平台“Terrasse”,露台或者天井,因为不管是工作开会还是放松休息,在露天的地方孵孵太阳大概算是我最低的人生趣味。博客还有个副标题——家·思·趣,所以在这里我会讲讲家庭,思考和兴趣的内容。家庭与兴趣比较好理解,思考么,认得我的人,大概都晓得,我是喜欢自己重新考虑问题的——这并非是说大多数人总是错的,而是我总是喜欢想想“替代方案”;而我莫名其妙的各色兴趣,更是有得一讲。